在許多亞洲家庭的廚房裡,味精早已是調味的靈魂。然而,這種名為「谷胺酸鈉」的白色粉末,卻也曾一度被妖魔化為「餐桌上的大魔王」。我們為何對味精心存恐懼?這背後不只是科學問題,更牽涉到文化、歷史、甚至種族偏見。
從昆布湯的靈感開始
故事得從1908年的日本說起。東京大學的化學教授池田菊苗,一天晚餐時品嚐到妻子熬煮的昆布湯,感覺其中有一種特別的「鮮味」,既不同於甜、酸、苦、鹹,也難以用語言形容。他稱這種味道為「umami」,結合日語中「美味」與「味道」的詞根。 他將數十斤昆布搬進實驗室,從中提取結晶,成功分離出一種透明晶體,谷胺酸。當這種物質與氫氧化鈉中和後,形成的谷胺酸鈉,也就是後來風靡全球的「味精」。 池田教授與鈴木製藥廠的鈴木三郎助合作,創辦「味之素」公司,開創味精商業化的先河。這種新型調味品,卻在日本本土受到強烈抵制,匠人們認為化學調味摧毀了傳統烹飪的尊嚴,媒體甚至以「蛇肉做原料」的流言攻擊味之素,導致輿論大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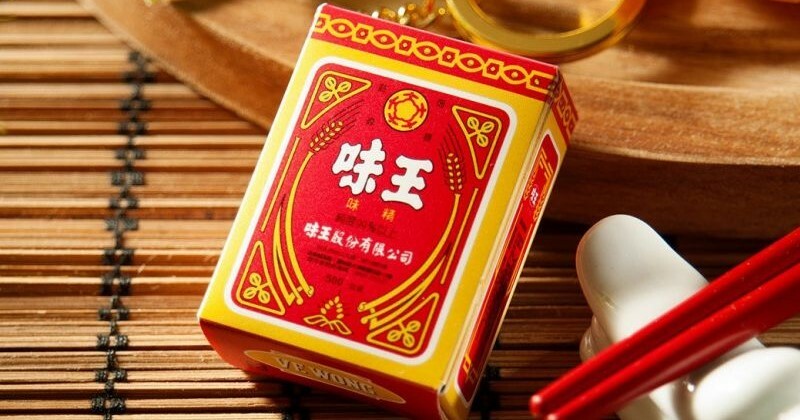
中國化學家的民族回應
1918年,味之素進入中國市場,迅速在上海打響名號。然而三年後,一位天才化學家吳蕴初出現,改寫了味精產業格局。 出生於書香門第的吳蕴初,在科舉廢除後自學化學,進入江南製造局工作。他發現味之素的核心成分僅為谷胺酸鈉,並從小麥與麵筋中模擬人體胃液消化過程,成功製作出成本更低的國產味精。他將產品命名為「味精」,意指「味道的精華」,並與張亦雲合作創辦「天廚」公司。 1923年起,「佛手牌」味精正式問世,以植物性來源為主打,符合佛教徒與素食者需求,很快便與味之素分庭抗禮。此後,更取得英、法、美三國專利保護,成功出口,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代表作。
細菌與技術:第三代味精誕生
1957年,一位來自台灣的年輕人蘇遠志於東京大學研究細菌發酵。他的突破點是找到一株可以「吃蔗糖、產味精」的特殊細菌,成功以發酵法大量生產味精。這項技術不僅大幅降低成本,更推動味精進入工業化量產時代。 蘇遠志與台灣味全公司合作,將這種細菌帶回台灣,自此開啟味精新紀元。價格低廉的味精大量進入市場,卻也為它的惡名埋下種子,便宜、人工、工業產品,逐漸成了負面標籤。
從醫學期刊到社會恐慌
1968年,一封由「羅伯特·浩明郭」署名的讀者來信刊登於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》,信中提到他在中餐館吃飯後出現脖子麻木、心悸等症狀,懷疑與味精有關。編輯不知是有意還是炒作,將此信件冠以聳動標題《中餐館症候群》。 此舉一石激起千層浪。短時間內,媒體接連報導各種與中餐有關的不適反應,從偏頭痛到心悸無所不包。1969年,一位名為約翰的醫生更在實驗中聲稱,向恆河猴注射大量味精會造成腦損傷,他甚至警告孕婦不要接觸味精,否則會導致胎兒腦部發育異常。 這些言論雖缺乏科學實證與雙盲實驗支持,卻因媒體與社會氛圍而迅速發酵,將味精徹底妖魔化。西方中餐館紛紛貼出「不含味精」的標語,反而強化了公眾對味精有害的既定印象。
被誤解的科學:谷胺酸的真相
根據加拿大約克大學N博士的研究,味精的主要成分,谷胺酸,是人體內可自行合成的非必需胺基酸。人體每天大約會合成50克谷胺酸,總量可達2公斤,廣泛存在於腦部與神經系統,負責神經傳遞訊號。 食用味精所攝取的谷胺酸,根本無法穿越血腦屏障,更不可能對大腦造成損害。至於注射高劑量所產生的實驗結果,對普通人飲食無參考意義。 味精當中的鈉離子也與氯化鈉(食鹽)相仿。30克味精的鈉含量僅相當於10克食鹽,換句話說,適量食用遠低於造成健康問題的劑量。 甚至還有韓國民眾曾被報導,連續38年每日食用味精,身體仍健康無虞。
從偏見回歸常識
最具諷刺的是,2018年,一位名為霍華德的醫生坦承,當年那封震驚社會的《中餐館症候群》來信,竟是自己與朋友打賭後寫的惡作劇,名字也是虛構。即使他曾多次致電雜誌社澄清,對方卻以損害權威為由拒絕撤稿。 至此,真相逐漸水落石出。味精風波,其實是種族偏見、媒體炒作與科學素養不足的合成品。真正該擔心的,不是味精,而是我們如何被輿論與標籤左右了判斷力。
尾聲:回歸味道本身
今日我們仍能從昆布、香菇、魚肉、火腿等天然食材中獲得鮮味,其核心也正是谷胺酸與其他風味胺酸(如肌胺酸、鳥胺酸)的結合。雞精正是這些胺酸的複方產品,比味精更加濃縮。 從昆布湯到味之素,再到天廚與味全,味精的歷史是一段科學、商業與文化交織的故事。它不是罪魁,也不是萬靈丹,而是我們文明進程中一段極具啟示的化學演化。
